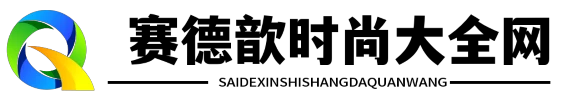一个勺子的对称美学乡村静止vs城镇漂移

说起《一个勺子》,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或许都是跟王学兵有关的危机营销,多舛的命运让这部电影的外围故事增添了不少唏嘘感叹。就像禁片往往更能引起猎奇心理一样,公众心中的标尺总是更喜欢向所谓的弱势方倾斜。未免买椟还珠了。
从金马奖到金鸡百花,陈建斌凭借《一个勺子》拿下了两座最佳新导演的奖杯,总不该是因为文本之外的故事吧?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导演,陈建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端出了好菜,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一个勺子》在谋篇布局和影像搭建方面,体现出的美学巧思。在接受1905电影网专访的时候,陈建斌详尽地为我们解读了很多细节背后的意义。

构图:对称的静止与流动 是乡村与城镇间的鸿沟
喜欢在构图上花心思做文章的导演都是值得另眼相看的。这种躲在情节进展背后的基础性表达元素,通常能润物无声地烘托出影片的整体气质。例如去年收获无数赞誉的《布达佩斯大饭店》,韦斯·安德森对于对称式经典构图近乎的追求,就为该片换来了精致考究的审美体验。而《一个勺子》也让我们惊喜地看到了大量质朴又古典的构图手段,大部分镜头都喜欢用窗棂、桥洞、炕和烟囱等规则图形作为依托,采取静态的对称模式,这种作者化的电影语言在现今的中国院线电影中其实已经为数不多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影片中村屋内部的镜头,一张大炕填满了整个房间的一半,连着烟囱的炉子又将炕劈成两半,陈建斌和蒋勤勤常常一人占据一边,台词不多,有时候也是静默地对抗。“从构图来说,西北农村的屋子本来就是那样,炕前面有个炉子,然后对面的部分就是客厅,取静态图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农村的生活状态就是那样的,完整的、缓慢的,基本是静止不动的。”陈建斌说,这种对称的构图方式所表达的其实是中国乡村凝重而迟滞的原生态,就像西北农民在房屋建筑上简单守旧的几何格局一样,他们的生活也是单调乏味的,没有互联网和手机带来的信息轰炸,充其量就是一台型号落后的彩电,机械地播放着农民更青睐的戏曲节目。
然而当陈建斌饰演的拉条子进城找大头哥的时候,静默的画面就会伴随着《最炫民族风》的旋律晃动起来。“一到城里之后,我都没有拍大头哥他们家,大头哥的家其实就是他那辆车,他那辆车是运动的,是不停地奔向各个不同的地方的。这是对城市和乡村的最大差异化描写,一个飞速移动,一个静止宁静。”影片中陈建斌身处城镇的部分,对称式的静态构图就被打碎了,大头哥将他那辆汽车称为“猛禽”,而机动车在拉条子夫妇眼中也确实就像一群吼叫着的野兽——当两辆摩托车从蒋勤勤身边呼啸而过,她吓得蹲在了地上。
这也是陈建斌在选择乡村题材时更想表达的观点: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漂移动荡的词汇,在这种动荡的背后,很多传统的社会价值标准也在摇晃中发生变化。

结构:宝塔诗的对仗呼应 是价值标准的两极碰撞
说到价值标准的变化,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个勺子》的故事结构了。电影讲述的是一个老实人,一番好意收留了一个傻子,还到处贴告示寻找他的家人。结果家人没找到,反而招来了南腔北调的人贩子。而老实人身边的聪明人都说,好端端地把一个傻子领回家,这种事也只有傻子干得出来。
从“遇见勺子”到“成为勺子”,影片在叙事上也采用了对称式的结构:金世佳饰演的勺子有一顶残破滑稽的遮阳帽,最后陈建斌将它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勺子在开头被一群熊孩子们欺负,拉条子出手相救,而当他的价值观崩塌之后,自己也成为熊孩子们攻击的勺子。在陈建斌的创作图纸中,这样的对仗化前后呼应其实很像一种叫做“宝塔诗”的文体:从一字句或两字句的塔尖开始,向下延伸,逐层增加字数至七字句的塔底终止,而《一个勺子》的布局则类似于一种变形宝塔诗,如塔之临水,塔影倒映,这也是一种对称的美感。
“时代是流动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时代的快速流动让农村和城市之间出现了鸿沟,与此同时也带动了一些价值标准的变化。拉条子真的是傻吗?他只不过是遵从了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个美德,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美德看起来很笨呢?这就是我们内心标准的一个变化。”陈建斌认为,《一个勺子》探讨“善”和“傻”这两个原本不该是矛盾体的人物特质,最终的落点还是在良知和两者之间的人性辩题。而无论是静态的对称构图,还是静态与动态的二元对立,亦或是“傻”和“不傻”的戏剧化呼应,也都是他在看到《奔跑的月光》之后所感悟到的故事魅力。
“我不号召任何东西,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给不出任何答案。但就我个人来看,有些东西是几千年来老祖宗传下来的,是有它的道理的。”陈建斌一字一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