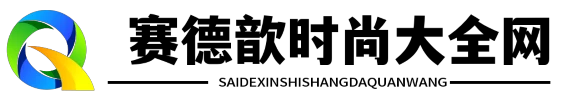话剧风云儿女首演演绎血光与勇气中大写的人
再现了田汉的话剧《风云儿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等重要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

前不久,在中戏昌平校区观看了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出品的话剧《风云儿女》首演。此剧以大量历史文献为基础,展现了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田汉先生激昂坎坷的一生,再现了田汉的话剧《风云儿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等重要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
此剧通过田汉、夏衍、聂耳、徐悲鸿、安娥、任光等人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面对艺术创作、爱情和生命的思考与行动,来推动整体剧情的发展;从人性的角度,探索人心深处关于生命和信仰的选择。它塑造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不畏艰险、舍生取义的文艺工作者群像,交错呈现诸多历史风云人物如何以文艺作品为武器,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唤醒民众的左翼文化运动中。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艺术地再现了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主创们共同寻找一个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结合点。从1929年田汉先生写出话剧《孙中山之死》、南国社赴南京公演说起,把相关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对比、穿插多条线索的戏剧结构中依次编织进来,将重要历史节点连缀成章,浓墨书写几位在黑暗境遇里苦寻信仰的人、将个人境遇不萦于心的人和相信天地总有澄明之时的人。他们用才华横溢的文笔和赴汤蹈火的血肉之躯,融汇成一条奔腾的河流,凝聚为一种精神上的传导。
舞美设计需要构建出复杂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内容范畴。多组道具营造出了多层次的视觉空间,结合话剧本身的语言逻辑共同推进情节,有回溯有瞻望。舞台上三组沿幕侧幕,以扭曲倾倒的造型和铁锈斑斑的质感,营造出危险动荡的时代氛围。对于影响新中国文艺发展历程的几部经典作品,通过呈现其创作过程,指向渐趋明朗的人物命运。相隔数年、不同角色的命运情境得以灵动地衔接、组合,人物在时空中不断跳进跳出,实现叙述的自由。
多重光影内容的叠化,诗意的视觉语言呈现出光与暗、安宁与沉重、伤痛与温暖的兼容。在那个时代最冷酷的至暗时刻,密不透风地布满着无数声音和讯息。田汉东渡日本求学,本被期望成为家,可他偏偏迷上了艺术,爱上了唯美的、感伤的气息,爱上了一种悲哀的生活。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实不容他沉溺在唯美的艺术里。作为作家,田汉直面正在裂变的中国时产生的惘然与迷失,使其与安娥之间的爱情产生得顺理成章,又充满宿命式的痛苦、无奈、爱恨交织。
编剧没有一味塑造田汉作为中国话剧奠基人的光芒,而呈现了他的多情、懦弱、逃避、不成熟等侧面——这是对生活敏感、对际遇深沉、对命运抗争的人,必然而正常的反应和想法。正由于表现出了这一点,揭露出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迷茫彷徨的懦弱面,才使人物鲜活、丰满、立体、可信,有现实的力量。
全剧善用各种情境“对比”来呈现和延伸人物生存与精神的种种矛盾冲突,自我突破与信念建立往往也是诞生在对立之中。例如田汉对信仰的坚定抉择映衬着对爱情的优柔寡断,忆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例如田汉在狱中修改《风云儿女》,同台并置着聂耳在旅馆狭小的房间里内心翻涌,终于找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用精妙的重要节点设计,展现出战争中真正的人间底色——人性极限时的纠结或崩溃,世界观的冲撞与模糊,人物在人生重要抉择时暴露的脆弱或觉醒。
剧中,穆时英为代表的“软性电影”与夏衍、田汉为代表的“硬性电影”之争,也能引发深层的思考。它们是电影艺术的一体两面,立意、内容、形式、倾向都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文艺创作在不同时代的追求,会呈现出一种所谓的割裂感。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话剧艺术正处于概念模糊混沌的年代,左翼艺术家们如盘古开天辟地,劈开这团混沌,让黑暗的天空出现了一条裂缝,唤醒沉睡迷惘的国人。那个年代文艺最重要的任务是激发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最需要的是对抗敌爱国的讴歌和强调。
而当时“软性电影”提倡的艺术快感论,宣扬电影是为了人的艺术,以人的感官与身体为衡量标准,反对空洞的宣传和枯燥的思想教育。这些“以人为本”的艺术标准,在近百年后的当下也成为我们思考的对象。文艺创作在不同时代的标准和目标看似大相径庭,实际上如果把目光放远,我们会发现,这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成长曲线。
结尾时,年近七十岁的田汉即将走完人生最后的日子,他与夏衍的幻影进行的对话升华了主题,带给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两位杰出的艺术家虽是意难平,但回顾无悔的一生,仍然相信早晚会有天地澄明的一天,个人的毁誉不必萦怀。这些历经了岁月洗礼、见证了时代变迁的艺术巨匠,向成败、功过、荣辱撰写的历史探问和自解。在血光与勇气的洗礼中,我们看见了顶天立地大写的“人”。